CopyRight © 2015 - 2016 学生云管理平台 All Rights Reserved.
技术支持:华文融媒云
京ICP备12019430号-5 公安机关备案号:11010802022717
作者 钟世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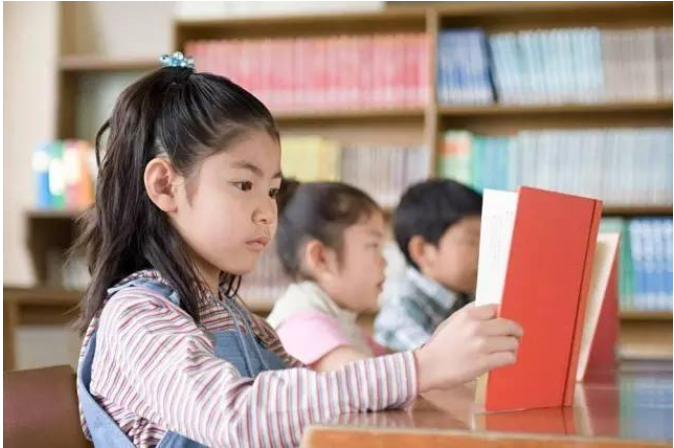
与速度对应的是量。量很重要,但在读书里,最好还是不要将它作为一项指标很刻意地列出来,学生阅读尤其不应该把“大量阅读”“海量阅读”当成这样一种刻意的目标来考察。语文课标里有阅读量的下限规定,虽然量实在是不多,也难免以“标准”的话语方式造成误导,让学生从小养成贪多求快的读书陋习。
我发现,许多“新”同学每次来到“吾班书屋”借阅图书时,喜欢东翻西翻,全无目的,又都希望能找到一本最好看的书,结果却好像并不满意。这也许跟我刚接手他们,还来不及给他们做读书推荐有关,但不完全是因为这个问题。
因为我还看到,许多同学的书读得过于快速,头天借走的书,第二天清早就会来退还。一天读完一本书,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,都不是太值得提倡的好现象,这与我一直在强调的“把书读慢”太相悖。
把书读慢的同义语是把书读进去。上面的第一个问题,就与没有把书读进去有更大的关系。因为没有读进去,不能将书读得慢下来,也就不能真正体会到一本书的好。许多的好书,就是这样明明已经到了我们眼里,却还是与我们擦肩而过,必须等以后再听到别人都在说它的好,才有可能重新去发现它的好。这真的不是个好习惯。
一路走来,和学生们将书读过来读过去,我发现我更喜欢这样的读书场景:几十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,满脸神情超逸,满室鸦雀寂声,其间有某一个人一字一句朗读某一本书的声音,像雨点和雨丝落入湖面;或者一个人静坐在那里默读,让这样的声音只落在自己心里——这是最美的默读,最美的默读是响在心底里的朗读:世界静下来,时间慢下来,每一个字,都掷地有声,耳朵听不见,但心听得见。
尽管学生们早已经会自己读书,我还是会经常选定曹文轩的《青铜葵花》,作为对高年级学生进行文学教育、阅读教育的朗读教材。此书纯美如诗,读到深处还会让人数度垂泪。读它之前,必先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两件“怪事”——“五七干校”、“上山下乡”——以及电视连续剧《孽债》中的一些情节慢慢说起,而后把速度放得更慢,逐字逐句给学生朗读完全书。这种好书慢读带来的一点好处是,小学生中竟然也有人会主动去找曹文轩的纯文学书来读。
读书当品。读好书更如品。真正喜欢的好书不仅当慢读如品,还可以“回读”如反刍。柳哲在《“书痴”曹聚仁》中写曹晚年的回忆——
“真正引起我兴趣、百读不厌的,倒是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,先先后后,一本正经地总共读了一百多遍。我看《红楼梦》,不如俞平伯老师那么多,只读了七十多遍,《水浒传》呢,我只看了二十多遍。《三国演义》,我只看了两三遍。”
当然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,但这种慢的精神,却有普适意义。
不能动不动就为“速读”找借口:不能因为时代、社会的节奏加快,就让读书也要无条件地跟着加快,不能因为要博览群书,或者因为长大后要快速地读完一个文件,就要让读书从儿时开始进入快车道,也不能因为要“阅读能力”,就理直气壮地过分强调速度。速度只是阅读力中很小的一股力,除了需要速度,读书更是个需要时间、精力、脑力、静力、耐力的活。如果已经忙得实在没有时间,连悠闲地读完一句话、一段文的时间都没有了,就最好不要选择读书。至于中国古儒们大多也懂得“蜻蜓点水法”、“信马由缰法”、“囫囵吞枣法”,那终究与自己喜欢的好书无关。
与速度对应的是量。量很重要,但在读书里,最好还是不要将它作为一项指标很刻意地列出来,学生阅读尤其不应该把“大量阅读”“海量阅读”当成这样一种刻意的目标来考察。语文课标里有阅读量的下限规定,虽然量实在是不多,也难免以“标准”的话语方式造成误导,让学生从小养成贪多求快的读书陋习。
现在的报刊杂志上时常会见到世界年人均读书量的报道,中国的量比较少,年人均也就三五本,但如果真是人皆达到了这个量,也足够了。能够在一年的时间内扎扎实实读完三五本书,对于一般人来讲,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